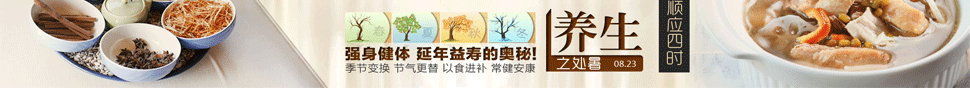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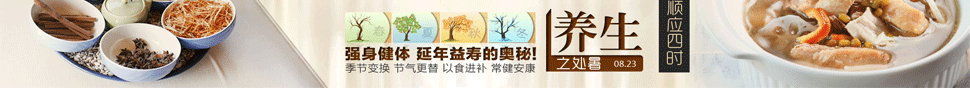
90年代的时侯买到徐志摩周年抒情诗歌曲辑,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磁带。其中有:《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沙扬娜拉》,《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山道旁》等诗歌,但现在的QQ音乐里找不到,我特意找出不同歌手唱的《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大家可听听。但我始终还是觉得不如当时磁带中韩磊唱的更入我心!
“这首诗的创作是徐志摩遇到林徽因时,心灵的天空总是被浓浓的情意和爱恋所笼罩,心音化作一只不知疲倦的鸟儿在不停地歌唱,觉得这就是一生的最爱,颠沛流离的心终于可以靠岸了。然而,命运多舛造化弄人,他并不是林徽因的唯一。于是,有了这首《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天使~在身边
.05.02
本文作者梁从诫,林徽因与梁思成之子03—昆明—
这确是一次历尽艰辛的「逃难」。年11月,我们在长沙首次接受了战争的洗礼。九死一生地逃过了日寇对长沙的第一次轰炸。那情景,在萧乾先生写的《一代才女林徽因》中,曾引用母亲自己的信,做了详尽的描述。
紧接着,在我们从长沙迁往昆明途中,母亲又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患肺炎病倒。我至今仍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们,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
林徽因在河北开元寺钟梁架上测绘
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这也是战争期间,我们家同那些飞行员之间,特殊友谊的开始。旅途中的这次重病对母亲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埋下了几年后地肺病再次复发的祸根。
年1月份,我们终于到达了昆明。在这数千公里的逃难中,做出最大牺牲的是母亲。
梁思成在五台山考察
三年的昆明生活,是母亲短短一生中,作为健康人的最后一个时期。在这里,她开始尝到了,战时大后方知识份子生活的艰辛。父亲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时时发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母亲也不得不卷起袖子买菜、做饭、洗衣。
然而,母亲的文学、艺术家气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昆明这高原春城绮丽的景色,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
梁思成在五台山考察记得她曾写过几首诗,来吟咏那「荒唐的好风景」,一首题为《三月昆明》,可惜诗稿已经找不到了。还有两首《茶铺》和《小楼》,在《林徽因诗集》出版时尚未找到,最近却蒙邵燕祥先生,从他保留的旧报上找出(披露在甘肃《女作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上)。
大约是在年冬,由于敌机对昆明的轰炸,愈来愈频繁,我们家从城里又迁到了市郊,先是借住在麦地村,一所已没有了尼姑的尼姑庵里,院里还常有虔诚的农妇,来对着已改为营造学社办公室的娘娘殿,烧香还愿。
林徽因与梁思成
后来,父亲在龙头村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而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
离我们家不远,在一条水渠那边,有一个烧制陶器的小村——瓦窑村。母亲经常爱到那半原始的作坊里,去看老师傅做陶坯,常常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然后沿着长着高高的桉树的长堤,在黄昏中慢慢走回家。
林徽因与梁思成她对工艺美术历来十分倾心,我还记得她后来常说起,那老工人的手下,曾变化出过多少奇妙的造型,可惜变来变去,最后不是成为瓦盆,就是变作痰盂!
前面曾提到,母亲在昆明时还有一批特别的朋友,就是在晃县与我们邂逅的那些空军航校学员,这是一批抗战前夕沿海大城市中,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后来大多数家乡沦陷。
梁思成
在昆明时,每当休息日,他们总爱到我们家来,把母亲当作长姐,对她诉说自己的乡愁和种种苦闷。他们学成时,父亲和母亲曾被邀请做他们全期(第七期)的「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
但是,政府却只用一些破破烂烂的老式飞机,来装备自己的空军,抗战没有结束,他们十来人便全都在一次次与日寇力量悬殊的空战中牺牲了,没有一人幸存!有些死得十分壮烈。因为多数人家在敌占区,他们阵亡后,私人遗物便被寄到我们家里。每一次母亲都要哭一场。
40年代的北平
04—重回北平—母亲爱北平。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早年的诗歌、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无一不同北平血肉相关。9年的颠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来了,像个残废人似的,贪婪地要重访每一处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记忆里那断了线的珍珠。
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躏,北平也残破、苍老了,虽然古老的城墙下仍是那护城河,蓝天上依旧有白鸽掠过,但母亲知道,生活之水不会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胜利后在北平,母亲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父亲应聘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但不久他即到美国去讲学。开办新系的许多工作,暂时都落到了母亲这个没有任何名义的病人身上。
她几乎就在病床上,为创立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同青年教师们建立了亲密的同事情谊,热心地在学术思想上,同他们进行了许多毫无保留的探讨和交流。
同时,她也交结了复原后清华、北大的许多文学、外语方面的中青年教师,经常兴致勃勃地同他们,在广阔的学术领域中进行讨论。从汉武帝到杨小楼,从曼斯斐尔到澳尔夫,她都有浓厚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
但是,这几年里,疾病仍在无情地侵蚀着她的生命,肉体正在一步步地辜负着她的精神。她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的生活。
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兴高采烈,滔滔不绝,以至自已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却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辍转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咯痰……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
她是那样地孤单和无望,有着难以诉说的凄苦。往往愈是这样,她白天就愈显得兴奋,似乎是想攫取某种精神上的补偿。
卧病在床的林徽因
47年前后地的几首病中小诗,对这种难堪的心境作了描述。尽管那调子低沉阴郁得叫人不忍卒读,却把「悲」的美学内涵表达得尽情、贴切。
年冬,结核菌侵入了她的一个肾,必须动大手术切除。母亲带医院。手术虽然成功了,但她的整个健康状况,却又恶化了一大步,因为体质太弱,伤口几个月才勉强愈合。
年的北平,在残破和冷落中期待着。有人来劝父亲和母亲「南迁」,出国、却得不到他们的响应。
抗战后期,一位老友全家去了美国,这时有人曾说.「某公是不会回来的了」。母亲却正色厉声地说:「某公一定回来!」这不仅反映了她对朋友的了解,也反映了她自己的心声。那位教授果然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举家回到了清华园。
年12月13日晚上,清华园北面彻夜响起怆炮声。母亲和父亲当时还不知道,这炮击正在预告着,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即将掀开新的一页。
解放军包围北平近两个月,守军龟缩城内,清华园门口张贴了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政治部的布告,要求全体军民对这座最高学府严加保护,不得入内骚扰。
同时,从北面开来的民工,却源源经过清华校园,把云梯、杉槁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运去。看来,一场攻坚战落在北平城头,已难以避免。忧心忡忡的父亲每天站在门口往南眺望,谛听着远处隐隐的炮声,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
他担心的,不止是城里亲友和数十万百姓的安危,而且还有他和母亲的第二生命——这整座珍贵的古城。中国历史上哪里有那样的军队,打仗还惦记着保护文物古迹?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当时中国真还有一支这样的军队。就在48年年底,几位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干部,坐着吉普来到我们家,向父亲请教一旦被迫攻城时,哪些文物必须设法保护,要父亲把城里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他们带来的军用地图上……父亲和母亲激动了。
「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从这件事里,他们朴素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直到他们各自生命结束,对此始终深信不疑。
05—解放—解放了。母亲的病没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姐姐参军南下,我进入大学,都不在家。对于母亲那几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没有细致的了解。只记得她和父亲突然忙了起来,家里常常来一些新的客人,兴奋地同他们讨论着、筹画着……。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荪林徽因(和一对儿女)、金岳霖过去,他们的活动大半限于营造学社和清华建筑系,限于学术圈子,而现在,新政权突然给了他们机会,来参与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实际建设工作,特别是请他们参加并指导北京全市的规画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作梦也想不到的事。作为建筑师,他们猛然感到实现宏伟抱负,把才能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的时代奇迹般地到来了。梁思成的北京设想图对这一切,母亲同父亲一样,兴奋极了。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过去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等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少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早晨统统加以实现。只有46岁的母亲,病情再重,也压不住她那突然迸发出来的工作热情。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因为新社会确实解放了她,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在旧时代,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写过诗,发表过学术文章,也颇有一点名气,但始终只不过是「梁思成太太」,而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分。梁思成的北京设想图现在,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画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份,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这不能不使她对新的政权、新的社会产生感激之情。「士为知己者用」,她当然要鞠躬尽瘁。林徽因设计的第一版国徽
那几年,母亲做的事情很多,我并不全都清楚,但有几件我是多少记得的。年,以父亲为首的一个清华建筑系教师小组,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工作,母亲是其中一个活跃的成员。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国徽,这也许是一个美术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也可能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机会。四版不同样式的国徽她和父亲当时都决心,使我们的国徽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徵,不仅要表现革命的内容,还要体现出我们这文明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他们曾担心:有人会主张像某些东欧「兄弟国家」那样,来一个苏联「老大哥」国徽的「中国版」。在最初的构思中,他们曾设想过以环形的璧,这种中国古老的形式,作为基本图案,以象征团结、丰裕与和平。现在的这个图案,是后来经过多次演变、修改之后才成型的。抱病设计国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年6月,全国政协讨论国徽图案的大会,母亲曾以设计小组代表的身分列席,亲眼看到全体委员,是怎样在毛主席的提议下,起立通过了国徽图案的。为了这个设计,母亲做了很大贡献,在设计过程中,许多新的构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她也曾多次亲自带着图版,扶病乘车到中南海,向政府领导人汇报、讲解、听取他们的意见……。正因为这样,她才会在毛主席宣布国徽图案已经通过时,激动地落了泪。周总理审议国徽新中国成立初期,她所热心从事的另一件工作,是倡导某些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改革。当时有人来向她呼吁,要挽救当时已濒于停顿、失传的北京景泰蓝、烧磁等手工业。她对这件事,给与了极大的关住,曾和几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一道,亲自到工场、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蓝等的制作工艺,观看老工人的实际操作。林徽因设计的夔龙纹对罐然后她又根据这些工艺特点,亲自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还亲自到作坊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在这个过程中,她还为工艺美院带出了两名研究生。可惜的是,她的试验在当时的景泰蓝等行业中未能推开,她的设计被采纳的不多,市面上的景泰蓝,仍维持着原来那种陈旧的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珐琅小罐
06—尽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年紧张的实际工作中,母亲也没有放松过在古建筑方面的学术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她和父亲以及莫宗江教授一道,在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将他们多年来对中国建筑发展史的基本观点,做了一次全面的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篇长文(载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建筑学报》)。林徽因与梁思成(青年)
这是第一次尝试着,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重新回顾从远古直到现代中国建筑发展的整个历程,开始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探求一个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在那几年里,母亲还为建筑系研究生,开过住宅设计和建筑史方面的专题讲座,每当学生来访,就在床褥之间,「以振奋的心情尽情地为学生讲解,古往今来,对比中外,谑语雄谈,敏思遐想,使初学者思想顿感开扩。学生走后,常气力不支,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吴良镛、刘小石:《梁思成文集·序》)。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年)
这里我想特别指出,母亲在建筑和美术方面,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对工作的要求也十分细致严格,而绝没有那种大而化之的「顾问」作风。这里,我手头有两页她的残留信稿,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为了不使我的这份记述成为空洞的评议,这里也只好用一点篇幅来引录信的原文,也可以算是她这部文集的一个「补遗」吧。
林徽因实地考察
年前后,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请她审稿并作「序」,她对其中彩图的效果很不满意,写信提出了批评,其最后几段如下:
青绿的双调和各彩色在应用上改动的结果,在全梁彩色组合上,把主要的对比搅乱了。如将那天你社留给我的那张印好的彩画样干,同清宫中大和门中梁上彩画(庚子年日军侵入北京时,由东京帝国大学建筑专家所测绘的一图,两者正是同一规格)详细核对,比照着一起看时,问题就很明显。
原来的构图是以较黯的青绿为两端箍头藻头的主调,来衬托第一条梁中段以朱为地,以彩色「吉祥草」为纹样的枋心,和第二条梁靠近枋心的左右红地吉祥草的两段藻头。两层梁架上就只出三块红色的主题,当中再隔开一块长而细的红色垫版,全梁青、绿和朱的对比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也不乱。
从花纹的比例上看,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给人的感觉非常安静,不像这次所印的那样浑圆粗大,被金和白搅得热闹嘈杂,在效果上有异常不同的表现。
青绿两色都是中国的矿质颜料,它们调和相处,不黯也不跳;白色略带蜜黄,不太宽,也不突出。在另外一张彩画上看到,原是细致如少数民族边饰织纹的箍头两旁纹样,在比例上也被你们那里的艺人们在插图时放大了。
总而言之,那张印样确是「走了样」的「和玺(木宛)花结带」,与太和门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画相比,变得五彩缤纷,宾主不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聒噪喧腾,一片热闹而不知所云。从艺术效果上说,确是个失败的例子。
林徽因实地考察从这段信中,不仅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专业的钻研,是怎样地深入细致,而且还可以看到,她在用语言准确而生动地,表述形象和色彩方面,有着多么独到的功夫(这本大型专业参考工具书后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参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这里,她和父亲一道,也曾为坚持民族形式问题,做过一番艰苦的斗争。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会被某种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抄得来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掉。母亲在「碑建会」里,不是动口不动手的顾问,而是实干者。53年3月,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我的工作现时限制在碑建会设计小组的问题上,有时是把几个有限的人力拉在一起组织一下,分配一下工作,做技术方面的讨论,如云纹,如碑的顶部;有时是讨论应如何集体向上级反映一些具体意见,做一两种重要建议。
今天就是刚开了一次会,有某某等连我六人前天已开过一次,拟了一信稿呈郑主任和薛秘书长的,今天将所拟稿带来又修正了一次,今晚抄出大家签名明天发出,主要要求:
立即通知施工组停扎钢筋;美工合组事虽定了尚未开始,所以趁此时再要求增加技术人员加强设计实力,第三,反映我们认为去掉大台对设计有利(原方案碑座为一高台,里面可容陈列室及附属设施——梁注),可能将塑型改善,而减掉复杂性质的陈列室和厕所设备等等,使碑的思想性明确单纯许多。……
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北京家里(年)除了组织工作,母亲自己又亲自为碑座和碑身,设计了全套饰纹,特别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为了这个设计,她曾对世界各地区、各时代的花草图案,进行过反覆对照、研究,对笔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
我还记得那两年里,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边的,几乎每一个纸片上,都有她灵感突来时,所匆匆勾下的某个图形,就像音乐家们匆匆记下的几个音符、一句旋律。
病榻中的林徽因然而,对于母亲来说,这竟是一支未能完成的乐曲。从54年入秋以后,她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了。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她的眼睛虽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
大约在55年初,父亲得了重病入院,紧接着母亲也住进了他隔壁的病房。父亲病势稍有好转后,每天都到母亲房中陪伴她,但母亲衰弱得已难于讲话。
病榻中的林徽因
3月31日深夜,母亲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父亲。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年仅51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前,悄然地离开了人间。那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母亲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则由父亲亲自设计,以最朴实、简洁的造型,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十年浩劫中,清华红卫兵也没有放过她。「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几个字,被他们砸掉了,至今没有恢复。作为她的后代,我们想,也许就让它作为一座无名者的墓留在那里更好?
母亲的一生中,有过一些神采飞扬的时刻,但总的说来,艰辛却多于顺利。她那过人的才华施展的机会十分短暂,从而使她的成就与能力似不相称。那原因自然不在于她自己。
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校园合影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文艺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同时,所有这些在她那里,都已自然地融会贯通,被她娴熟自如地运用于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得心应手而绝无矫揉的痕迹。不少了解她的同行们,不论是建筑界、美术界还是文学界的,包括一些外国朋友,在这一点上对她都是钦佩不已的。
林徽因写给费正清夫妇信件手稿谈起外国朋友,那么还应当提到,母亲在英文方面的修养,也是她多才多艺的一个突出表现。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年来访时曾对我说:「你妈妈的英文,常常使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感到羡慕。」
父亲所写的英文本《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部分,就大半出自母亲的手笔。我记得五十年代初,她还试图用英文为汉武帝写一个传,而且已经开了头,但后来大概是一个未能完成的项目。
梁思成历代佛塔型类演变图
总之,母亲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也可以算是现代中国文化界的一种现象。年一些人在批判「大屋顶」时,曾经挖苦地说:「梁思成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古文好,洋文也好,又古又洋,所谓修养,既能争论魏风唐味,又会鉴赏抽象立体……」这些话,当然也适用于「批判」母亲,如果不嫌其太「轻」了一点的话。
20世纪前期,在中西文明的冲突和交会中,在中国确实产生了相当一批在不同领域中「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多少称得上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们是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林徽因书作他们的成就,不仅光大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也无愧于当时的世界水平。这种人物的出现,难道不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事?在我们中华文明重建的时候,难道不是只嫌这样的知识份子,太少又太少了吗?对他们的「批判」,本身就表示着文化的倒退。那结果,只能换来几代人的闭塞与无知。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只生活了短短6年时间,但她的思想感情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当时的新政权曾以自己的精神和事业,强烈地吸引了她,教育了她。
林徽因书作以她那样的出身和经历,那样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而能在短短几年里,就如此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信任、智慧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这新的国家、新的社会,甘愿为之鞠躬尽瘁,又是那样恳切地,决心改造自已旧的世界观,这确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
许多人曾对我说过:你母亲幸亏去世得早,如果她再多活两年,「反右」那一关她肯定躲不过去。是的,早逝竟成了她的一种幸福。对于她这样一个历来处世真诚不欺,执着于自己信念的人,如果也要去体验一下,父亲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所经历过的一切,那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我简直不敢想像。
金岳霖
文革期间,父亲是在极度的痛苦和困惑中,顶着全国典型「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死去的。我只能感谢命运的仁慈,没有让那样的侮辱和蹂躏,也落到我亲爱的母亲身上!
年,在母亲的追悼会上,她的两个几十年的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蜇联名给她写了一副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父亲曾告诉我,《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是母亲在我出生后的喜悦中,为我而作的,但母亲自己从未对我说起过这件事。
无论怎样,今天,我要把这「一句爱的赞颂」,重新奉献给她自己。愿她倏然一生的追求和成就,化作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财富,如四月春风,常驻人间!
作者系林徽因与梁思成之子梁从诫
一九八五年四月北京一稿
一九八六年四月北京二稿
戳“阅读原文”查看上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