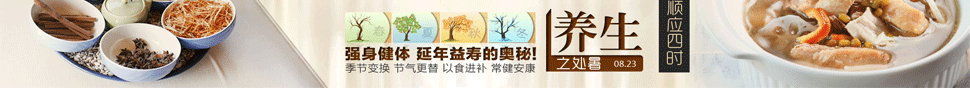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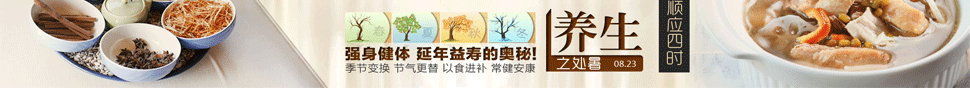
导言:本文是对于原来《印度文明的轴心突破》一文中佛教部分的扩展。原文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突出佛教之“无生”论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所以对于佛教的论述以龙树菩萨之“中观”为核心,因《中论》于“无生”之义论之最为精要。
考虑到有不少读者希望能对于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显宗)有更完整的把握,就对原文做了扩展,着重补充了“瑜伽行”(唯识)与“如来藏”部分的论述,由“如来藏”而入“不二法门”。讨论“不二法门”之《维摩诘经》,虽为大乘显宗之经典,实已通于密乘。此正“不二”之真意也。
佛陀与佛教
佛教之名,源于其创始人将自己称为佛陀(budhha“觉者”)。这种命名指示出佛教与其它宗教的根本差别:佛教不承认作为超越者的神与作为有死者的人之间的绝对差别,佛陀与最平凡乃至最卑贱的众生之差别,只在于是否觉悟。佛陀是究竟觉悟的众生,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陀。在此意义上,佛教是最平等的宗教,甚而超脱于宗教。作为佛教创始人的佛陀,因其出生于释迦(?ākya)族,故称“释尊”。有关其出生时代,有多种说法。较常见的一种是,他在公元前年生于迦毗罗卫城(Kapilavastu)的王室家庭,本名乔达摩·悉达多(GautamaSiddhattha)。注:依各种佛教文献的记载,释尊于80岁入灭。因而其出生年代可由其入灭年代加以推算。依据南传的锡兰《岛史》(Dīpava?sa)与《大史》(Mahāva?sa)之记载推算,佛陀于公元前年(亦有说为前年或前年)入灭,故其生年当在公元前年。
若依据北传的说法,释尊入灭与阿育王即位相隔年,若阿育王于公元前年即位(亦有说为公元前年或前年),则释尊当于公元前年入灭,其生年则在公元前年。此二说年代相差近百年,颇难调和。
本文出于行文方便,取释尊在世年代为公元前年-前年说。
他作为释迦族的王子接受极好的四吠陀与五明教育,娶妻生子,直到二十九岁那年,因“四门出游”见证生老病死之苦(各类佛教文献如《佛行所赞》对此有非常富于戏剧性的描写),当夜为求究竟解脱之道毅然离宫出家[据《大般涅槃经》,释尊为“追求善(kusala)而出家”]。注:五明(pa?ca-vidyā)包括1.声明(?abda-vidyā),音韵训诂之学;2.工巧明(Silpasthāna-vidyā),工艺技术之学;3.医方明(Cikitsa-vidyā),医药之学;4.因明(Hetu-vidyā),逻辑推理之学;5.内明(Adhyātnā-vidyā),宗乘大意之学。
在周游求道的过程中,他向数论和瑜伽之大师学习一年而犹未满足,进而实行最严格的苦行长达六年,在此期间,他开始被人尊称为释迦牟尼(?ākyamuni,“释迦族的觉者”)。当他终于明了苦行于解脱无益,在接受一位信女供养的乳糜奇迹般地恢复元气后,于伽耶(Gaya)村的阿说他树(a?vattha,后因佛陀在此树下成道而被称菩提树)下,敷吉祥草入金刚座,发愿不成正觉(abhisambodhi)不起此座。经过四十九天的返观内照,以见明星升起之契机,终于证悟“无上正等正觉”(anuttara-samyak-sambodhi)。据《华严经》记载,佛陀证道后最初的感叹是:“奇哉!奇哉!此诸众生云何具有如来智慧,愚痴迷惑,不知不见?我当教以圣道,令其永离妄想执着,自于身中得见如来广大智慧与佛无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一《如来出现品》)。佛陀成道后赴波罗奈城的鹿野苑(M?gadāva,今Sārnāth)对曾与其同修的憍陈如等五人讲法,此五人俱得阿罗汉果(Arhatvaphala),当即皈依佛陀出家。以究竟觉悟之佛陀为佛宝(Budhha-ratna),佛所开示之教法为法宝(Dharma-ratna),五阿罗汉为僧宝(Sa?gha-ratna,僧原指佛教修行者之团体,后泛指一切依佛教法修行的出家沙门),三宝(tri-ratna)具足,佛教得以形成,而三宝也成为了佛教的代称。"三藏"形成与佛教的分裂
在此后的四十九年里,佛陀一直致力于让众生悟入佛之知见,于整个印度次大陆弘法。在此过程中,佛教僧团组织与信众数量不断增长,刹帝利阶层表现出对于这一新兴宗教的极强烈的追随态度,吠舍(自由民阶层)和首陀罗(底层平民与贱民)也是其积极的支持者,甚至婆罗门阶层中都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改宗皈依者,佛陀十大弟子中的摩诃迦叶(Mahāka?yapa)和舍利弗(?āriputra)便出身于婆罗门家庭。这是自吠陀传统确立以来印度社会整体思潮之大变化。针对佛教在全印度广泛传播的情态,佛陀采取了允许弟子用除梵语之外的各地方言传教的语言政策。这一灵活的语言政策不但让佛教得以有效融入各地之生活实际,也推动了各地俗语的雅语化,巴利语(Pali)作为早期佛教传播史上最重要的语言,正是这种带有雅言特征之俗语的代表。公元前年11月,佛陀于世寿八十岁之年在吠舍离城(Vai?āli)附近的波梨婆村(Beluva)圆寂,临般涅槃之际,他针对阿难(Ananda)所作之四个问题,开示弟子们,在佛入灭后,要以戒为师、以四念处安住、以默摈置之调伏恶人、在一切经首安立“如是我闻”令人起信。据佛教文献记载,在佛陀入灭后至奠立孔雀王朝统一印度并皈依佛教的阿育王(A?oka,公元前年左右即位,在位36或37年)统治期间,佛陀弟子与信众进行了三次集结(sa?gīti,“齐诵”),对佛教教义进行了三次成规模的整理,形成了那个时代的佛教主要经典体系。这一体系大致可分为经藏(sūtra-pitaka,巴利语sutta-pitaka,佛陀亲自宣说之经典)、律藏(vinaya-pitaka,巴利语同,佛陀所制定的律仪)、论藏(abhidharma-pitaka,巴利语abhidhamma-pitaka,对佛典经意之阐发论述)三部,三藏之名也成为了一切佛教教义的统称。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发生了佛教内大众部(Mahāsā?ghika)与上座部(Sthavira)的分裂。这一分裂对于佛教教义的演化影响极为深远,某种程度上,大众部是大乘佛教(Mahāyāna)的先声,而上座部则是小乘佛教(Hīnayāna)的最典型代表,由它又衍生出一系列其它的小乘部派。注:有关佛教分派的记述,史料不少。这些史料又主要分为南传与北传两大类。
南传史料代表典籍是《岛史》(Dīpava?sa)、《大史》(Mahāva?sa)及《论事》(Kathavatthu)等;北传史料代表典籍是《异部宗轮论》(Samayabhedoparacanacakra-?astra)、《部执异论》(《异部宗轮论》的异译本)、《异部宗精释》(Nikayadabheda-vibhā?gavyana)。有关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分裂,南北传均认为在佛灭后百年,但原因则颇不同。依律藏《七百犍度》所载,分裂是因为在毗舍离(Vasāli)的比丘就是否违反戒律的十种问题(“十事”)进行的审议,此十事在二百五十戒中被禁止但许多比丘要求放宽的事项,其中的“金银禁”(禁止比丘受持金银财物)更特别引发诤论。
依北传的《异部宗轮论》,分裂则是源于长老大天(Mahādeva)提出的五个主张(“大天五事”),都与传统上有关阿罗汉之境界修证的说法不同:1.余所诱(阿罗汉为天魔所诱仍会漏失);2.无知(阿罗汉仅断染污无知,尚未断尽不染污无知,尚有疑惑存在);3.犹豫(疑有“随眠之疑”与“处非处”之疑二种,阿罗汉尚未断尽后者,仍有惑相现前);4.他令入(阿罗汉须依他人之记别,方知自己已得解脱);5.道因声故起(阿罗汉虽已有解脱之乐,然至诚唱念“苦哉”,圣道方可现起)。南传上座部的《论事》于此也记载。有可能“大天五事”与“十事”是这一时期相续发生的事件。
小乘与大乘: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
佛教中小乘与大乘之名,是大乘佛教兴起后所生。二者常常与佛教传播的历史与地理情况联系起来:小乘往往指自印度流播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地区的南传佛教,大乘则往往与流传于中国与东北亚的佛教相关。就语言而言,小乘佛典使用巴利文,经典文本大约成形于公元前五世纪;而大乘佛典使用梵文(包括带有某些俗语特征的混合梵语),最早的大乘佛教文献《般若经》出现于公元前一世纪末。注:日本学者辛岛静志在《法华经中的乘(yāna)与智慧(j?āna)》一文中提出,“智慧”“修行道”(乘)的变化基于梵语话过程中把原本意义为“智慧”的jāna错误地梵语化为yāna,大乘(mahāyāna)的提法可能源自mahāj?āna“大智”,本意为“佛智”。
如果单纯从文献问世的时间而言,大乘经典往往会被认为是佛教思想在特定历史境遇下对原初教义的创新和发展。然而,从大乘佛教的立场而言,则一切大乘经典,无不是佛陀的真实开示,经典形诸于文字较晚,只是因为此前的因缘尚未成熟。而因缘,正是一切佛教派别皆认同的基本教义。因缘(nidāna)或缘起(pratītyasamutpāda),是指各种现象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一切诸法(dharma,事物、现象以及对于现象的意识)无不是因缘和合而生,又以因缘之迁变-消散而转化-消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一切诸法,以其由因缘和合而生,究其根本,均无恒常不变、独立存在的自性或实体,此即“无常”(anitya)-“无我”(anātman)义。以无常-无我义观之,则印度教最高明玄妙之范畴“梵-我”(Brahman-ātman),也无非是一种特定的妄想执著罢了。缘起,是佛陀证悟之“自受用”(自修自证),为方便度化众生而演述缘起之理,则是“他受用”,“四谛”正是“他受用”之始。“四谛”,即四种真理之义,分别为"苦"(du?kha,处在轮回中的一切众生状态根本是苦)、"集"(samdaya,各种痛苦之因招致汇集各种痛苦之果,根本在于欲望,欲望在于无明)、"灭"(nirodha,彻底消灭欲望与无明,从而消灭痛苦之因,实现超越轮回之解脱)、"道"(mārga,达致解脱的方法与道路,即修行实践)。实现灭苦之法的“苦灭道圣谛”,被表述为“八正道”(āryao?a?gika-mārga):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正见是能如实了知自身与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见地,即以了知缘起为核心的整体世界认知,是八正道的基础。基于正见而有正确的思维(正思维)、正确的言语表达(正语)、正确的行动与事业(正业)、正确的生活与生命方式(正命)、正确的努力(正精进),见地融入生活实际,则能保持正确的觉知与心念状态(正念),正念的持续深入,则能达到正确的禅定,即融止息妄念与如法观察事物实相于一体之止(?amatha)-观(vipa?yanā)双运的状态(正定)。八正道中,正见、正念、正定最为重要,分别代表着苦灭的基础、路径、成果。八正道又往往又被概括为戒定慧三学。“四谛”是小乘佛教所认同的最根本之真理,也是其修行体系的根基和旨归。对于大乘佛教而言,“四谛”以及与之相关的“十二因缘”,同样被认为是佛法的基础,但犹未以此为最胜境界,而往往将其对应于“声闻”(最高果位为阿罗汉)和“缘觉”(最高果位为辟支佛)的修行实践。大乘佛教承认佛法的核心在于缘起,但这一意义上的缘起含摄无尽,甚深微妙,它包含着十二因缘,但并不等同于十二因缘。注:十二因缘,是指无明(avidya)-行(sa?skāra)-识(vij?āna)-名色(nāmarūpa)-六入(oa”āyatana)-触(spar?a)-受(vedanā)-爱(t°o°ā)-取(upādāna)-有(bhava)-生(jāti)-老死(jarāmara°a)这十二个环节的相续与作用,有情众生正以此十二因缘之相续作用而于生死大海中轮转不息。
中土华严宗所概括的四种缘起中,于小乘教说业感缘起(十二因缘即属此),于大乘始教说赖耶缘起,于大乘终教说真如缘起(如来藏缘起),于大乘圆教说法界缘起。而藏传佛教宁玛派有业因缘起(格鲁派称相连缘起)、相依缘起、相对缘起、相碍缘起之四重缘起说。
汉藏两大传统中的四种缘起说,当各有印度佛教的来源,也各自所重,各受所植根传统之影响,如华严宗之于汉传佛教的判教说,宁玛之于藏传佛教的观修法门;华严宗将四种缘起视作四种不同教法的缘起见,彼此并无直接关联;宁玛则将四重缘起视作具一贯性而重重超越的观修整体。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根本差别在于:小乘以轮回为虚妄,以涅槃为真实,以摆脱轮回达于涅槃(nirva°a)为最高之修行目标,而大乘则以为二者皆幻,执着轮回则偏于幻象,执着涅槃则偏于幻象的消失,而轮回与涅槃究竟不二,两皆不住,方为中道;小乘以佛法为实有(dravya),而大乘则以一切诸法皆空,性空而幻有,即一切诸法皆无实在之自性,但可依因缘而生起幻化出假有的现象,故小乘只能做到“我空”,而达不到“法空”,而大乘则法-我皆空;小乘以阿罗汉为果位,修行上以远离俗事避世清修为主,而大乘以成佛为究竟,效仿出世-入世圆融无碍的菩萨(Bodhisattva“觉有情”)行事,故而不但可以介入世间法,更可以借世间法来砥砺、深化乃至圆满修行。龙树之“中道观”
在早期大乘佛教的传播弘法过程中,龙树(Nāgārjuna)发挥之作用至为重大,是后代大乘佛教各宗及密教所共同尊奉的祖师。他的著作极多,号称“千部论主”,其所传世之作品,以《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回诤论》等为代表,影响极深远。《中论》、《十二门论》与龙树传人提婆(Deva)所著的《百论》更是构成了汉传佛教三论宗的根本经典。特别可以重视的,是他提出的中道观(madhyamaka):“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ya?pratītyasamutpāda??ūnyatā?tā?pracakomahesāpraj?aptirupādāyapratipatsa?vamadhyamā《中论》第二十四品]中道,意味着对缘起法既理解为空(无自性),又理解为假名(即名相概念,以其无真实自性而方便施设而成,故名之为“假”)。因其空,故非有,因其假名,故非无,中道便是超越于有无的缘起。此义进一步宣说,即《回诤论》所言“佛说空缘起,中道为一义。敬礼佛世尊,无比最胜说”。空、缘起、中道,此三者实为一义,因而,空性应从一切现象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因缘中加以体认,缘起当从一切现象本无恒常、独立之自性加以理解,中道则意味着空性与缘起的无碍圆融,离有无二边,非有非无,亦不废有无。一切对立性质的概念名相莫不如是,此即《中论》篇首所言“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anirodhamanutpādamanucchedama?ā?vatam
anekārthamanānārthamanāgamamanirgamam]之境界,同样,“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nasa?sārasyanirvā°ātki?cidastivi?eoa°am
nanirvā°asyasa?sārātki?cidastivi?eoa°am《中论》第二十五品]。大乘佛教中,这种不落两边、融通世出世间诸法无碍之究竟智慧,被命名为般若。龙树所代表的中观,核心在说明般若之体性。而以弥勒(Maitreyanātha)为祖师、以无著(Asa?ga)、世亲(Vasubandhu)为重要传承者的瑜伽行派(Yogācāra),核心则在此般若体性之现证。
注:瑜伽行派将祖师弥勒与未来佛弥勒视作一人,故传世的弥勒著作往往被解释为无著在禅定中于兜率内院听法所记。归于弥勒名下的主要作品,在汉地的传承为“五论之颂”:
《瑜伽师地论》、《分别瑜珈论》、《大乘庄严经论颂》、《辩中边颂》(《中边分别论颂》)、《金刚般若经论颂》,在西藏的传承则为“弥勒五法”(Maitreya-pa?cadhrma):《大乘庄严论》(Mahāyāna-sūtrāla?kāra)、《中边分别论》(Madhyānta-vibhāga)、《辩法法性论》(Dharmadharmatā-vibha?ga)、《现观庄严论》(Abhisamayāla?kāra)、《宝性论》(《大乘无上续论》Uttaratnatra)。
在藏传体系中,《瑜伽师地论》(Yogācārabhūmi)的作者为无著。无著所著的《摄大乘论》,所撰集的《大乘阿毗达摩集论》,世亲所著的《摄大乘论释》、《唯识三十颂》、《十地经论》、《唯识二十论》,也是瑜伽行派极重要的作品。世亲所著《阿毗达摩俱舍论》虽不属于这一系列,但对瑜伽行派也有一定的影响。
弥勒瑜伽行之核心在于指导大乘行人之修学-修证,包含着法相、唯识、如来藏三个体系,以法相为基础,以唯识为路径,以如来藏为旨归。法相建立三自性(依《解深密经》、《中边分别论》,则为三自性相):遍计自性(parikalpita-svabhāva)、依他自性(paratantra-svabhāva)、圆成自性(pariniopana-svabhāva),分别对应于“所应知”、“所应断”、“应所证”的三个修证层次(《摄大乘论·无性释》),又立三无性,即相无自性(lakoa°a-ni?svabhāva)、生无自性(utpatti-ni?svabhāva)、胜义无自性(paramārtha-ni?svabhāva),以作为对三自性之超越。注:依世亲《三自性判定》(Trisvabhāva-nirde?a)中悟入三自性的次第,由遍知而无所得、由遍断而离所现、由证得而现证无二,则行者当由相无自性现观遍计自性相,从而现证其无自性,知其所应知,是为遍知;
由生无自性现观依他自性相,从而现证其无自性,知其所应断,是为遍断;由圣义无自性现观圆成自性相,从而现证其无自性,知其所应证,是为证得。
阿赖耶识、如来藏与“不二法门”
唯识(vij?aptimātratā)的核心,在于否定凡夫认为实在的认识对象,舍弃将外界执为实有的妄想,而体证“唯识”(即“只有识”)。更进一步,伴随对象虚妄性的消解,与其分裂-对立的“我”-“我执”之虚妄性亦消解。故而唯识意味着一种认识境界的转化:从境(对象)识皆有的状态,到境(对象)无识有的状态,到境识皆泯的状态。这种由凡夫到圣者的认识境界转化,被称作转依(ā?rayaparāv°tti),即转凡夫之识为佛智的过程(转烦恼障而得大涅槃,转所知障而得大菩提,此大涅槃与大菩提为“二转依之妙果”)。唯识延续了阿毗达摩体系中有关色法、心法、心所法、涅槃的诸法分类,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形成了色法十一、心法八、心所法五十一、心不相应行法二十四、无为法六的“唯识百法”体系。其中八种心法,正对应于唯识所言之“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前六识分别对应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第七末那识(mano-vij?āna)表将一切执为我有的思量(manas,为我执的根源),第八阿赖耶识(ālaya-vij?āna)之阿赖耶(ālaya)为“收藏”之意(“藏识”),是一切关系轮回生死等诸法种子(bīja)的集合体。如来藏(tathāgata-garbha),与作为阿赖耶识之根基的阿赖耶为同一体性。就其受业力染着的功能-境界而言,名为阿赖耶;就其不受染而本自清净之功能-境界而言,名为如来藏。如来藏为如来内自证智境,就其不被一切外缘所染本自清净而言,可称如来法身;就其可借种种因缘而于众生之识境自显现而言,可称如来法身功德。如来法身与如来法身功德恒时双运,意味着如来之内自证智境借众生识境而显现,也意味着,一切世界即借识境而显现的如来智境。小乘以无常、无我、苦为诸法之实相,而大乘佛教则言常、乐、我、净,这种认识差异之根本,在于大乘所言之常、乐、我、净实为如来藏之四德,对应于如来内自证智境:超越无常,离生、住、灭,故谓常;生机周遍,本自具足,一切诸法得自显现,故谓乐;如来法身即众生界,于一切法终不异离,故谓我;不离一切法,而如来法身终不变异,本来不污染,故谓净。《胜鬘经》提到有两种如来藏:空如来藏,“若脱、若离、若异一切烦恼藏”;不空如来藏,“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所谓空如来藏,对应于菩萨之修证,即通过修行转识成智、化种种烦恼归于清净自性,以其导烦恼于空性,故名为“空”。弥勒瑜伽行体系即致力于空如来藏之修证。至于不空如来藏,则为如来内自证境界,法尔清净,究竟平等,大悲周遍,无假于空(亦无假于修证),故名“不空”。注:如来藏系列的经典,包括《如来藏经》(Tathāgatagarbha-sūtra)、《央掘魔罗经》(A?gulimālika)、《不增不减经》(Anūnatvāpūr°atvanirde?a-parivarta)、《胜鬘经(《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rīmālāsi?hanāda-sūtra)、《解深密经》(Sa?dhinirmocana-sūtra)、《大乘阿毗达摩经》(汉译、藏译均不存,但无著之《摄大乘论》与《大乘阿毗达摩集论》均是基于此经所作)、《入楞伽经》(La?kāvatāra-sūtra)、《宝性论》(RatnagotravibhāgoMahāyānottaratantra-?āstra)
如来藏之教,亦可名为“不二法门”(advayadharmamukhaprave?a)。所谓“不二”,论之不尽,真空妙有不二,烦恼菩提不二,轮回涅槃不二,世间世出不二,有为无为不二,皆在其中。其真境界,则超越一切言语思维。这非但是大乘修证之胜境,也指示出一种修行的路径,即以特定的事相为方便求证其空性,通过事相所对应的不空之力用求证其本空之体性,因根本而言,体性与力用不二,方便即为究竟。注:说“不二法门”的,集中于以文殊师利为说法者的系列经典,特别是《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以文殊师利为重要参与者的《维摩诘经》(Vimalakīrtinirde?a-sūtra)。
《维摩诘经·佛道品》中,维摩诘问文殊师利:“何等为如来种?”文殊师利言:“有身为种,无明有爱为种,贪恚痴为种,五盖为种,六入为种,七识处为种,八邪法为种,九恼处为种,十不善道为种。以要言之,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为佛种。。。。。。。是故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
此如来种(tathāgatagotra)即是如来藏,不二法门即法身借烦恼而显现的如来藏。
佛教的流变
公元六七世纪开始,印度的大乘佛教吸收许多印度教之仪轨、神祇化为己用,形成了对于传授者具有严格的戒律受持要求的密宗,至八世纪则蔚然成风,转而为印度佛教之主流。这一方面是受到了当时印度教复兴,特别是商羯罗(?ankara)所创立之吠檀多新论的重大影响,但同时也是以中观为基、瑜伽行为道、不二法门为果之修证理路与实践的自然延续与发展。说“不二法门”的大乘显教经典《维摩诘经》,实已深通于密法,维摩诘非但是显教之大菩萨,亦是密乘行者。值得注意的是,商羯罗的理论根本的特点正在“无分别不二论”(advaita),其中吸收了大量中观派的学说,以致后来有印度教学者将其称为“伪装的佛教”。其后,佛教在印度逐渐式微,而密宗则自八世纪后传播于中国,形成了唐密与藏密两大支流,唐密又传到日本形成东密。生发于印度的佛教,于十三世纪初在印度归于寂灭,而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却始终繁盛,示现出某种特定的因缘。“无生”与“中道”
佛教于人类文明史之最重大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以“缘起性空”为核心的世界解释,它根本有别于以神祇信仰为核心的“创生论”和以生命之内在价值为核心的“生生论”,而指向在一切生灭现象背后的作为世界实相的“无生”。“无生”意味着,一切事物现象于因缘和合中,既非由自我所生,也非由他者所生,也非由自己和他者共同所生,也非无因而生,故知究竟无生,如《中论》第一品所言:“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nasvatonapiparatonadvābhyā?napyahetuta?utpannājātuvidyantebhāva?kvacanakecana]。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佛教不但给与了周严广大高明深切的思辨(philosophia),更提供了以亲证(sākoātkāra,本意“用眼观看所得”)为特征的修行指引。这种具足闻、思、修、证的体系,兼有哲学与宗教之面相,又超越哲学与宗教,以自己的存在体现着“中道”。
-END-
作者: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
欲获得文章完整版参考书目及注释可点击联系作者!
▽
论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克服
世界文明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主义
何谓“双天”—论旧约希伯来语中“天”(?×mayim)一词双数形式的来源及文化意义
从“承认的政治”到“觉悟的政治”
在“师生辩证法”的视野里:群众路线、结构化理论与制度变迁的相互观照
如何认识公有制、社会主义与国企改革
从主奴辩证法到师生辩证法:世界历史的“列宁时刻”与“毛泽东时刻”
不易、变易、简易—从中国传统看中国学派
从战略高度看待中美关系
“郭德纲版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新义谱系—在两友新书研讨会上的发言
自主赶超VS比较优势——毛泽东时代整体发展路径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何谓宗教?何谓神?:一种比较语言学-语文学的探索(下)
何谓宗教?何谓神?:一种比较语言学-语文学的探索(上)
中国民主的理论体系(三)——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观
中国民主的理论体系(二)——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与问题
中国民主的理论体系(一)——从古希腊到法国大革命
从制度自信到制度自觉-评《中国集体领导机制》
《革命与法权:宪法序言的某种解读》
↓
一种融合历史与现实、传承与创新、
经典阅读与生命经验的文明论视野。
大道之行天下文明
ID:ddzxtxwm
▲
长按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jixiangcaoa.com/hxcf/41988.html


